与魔鬼共舞:论人性中的“同情恶魔”悖论
在道德的天平上,同情常被视为人性的光辉,但当对象是“恶魔”时,这种情感便成了撕裂理性的利刃。从神话中的路西法到现实中的极恶之徒,“同情恶魔”的冲动揭示了人性中复杂的矛盾——我们为何会被黑暗吸引,甚至试图为其辩护?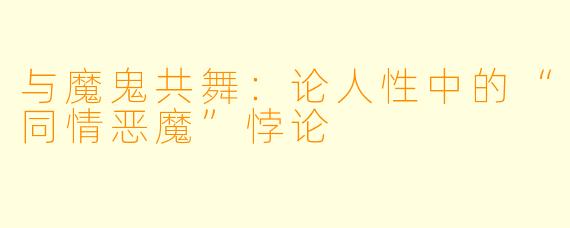
这种悖论或许源于对“绝对邪恶”的恐惧消解。当恶魔被赋予悲剧性的过往(如《失乐园》中堕落的撒旦),或当现实中的罪犯展现出脆弱一面(如庭审中哭泣的杀人犯),人们会不自觉地用共情稀释恐惧,以“理解”替代审判。心理学称之为“道德脱钩”——我们通过将恶行归因于环境或创伤,来维护自我对“人性本善”的信仰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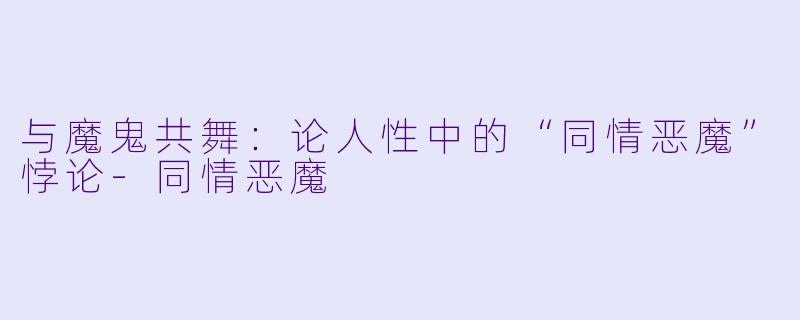
但危险正潜伏于此。尼采曾警告:“与怪物战斗者,需警惕自己亦成为怪物。”过度同情恶魔,可能模糊善恶的边界。二战后的汉娜·阿伦特在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中发现,纳粹军官的平庸面孔让世人震惊——恶魔未必青面獠牙,而可能藏在“我只是服从命令”的平凡借口背后。若连这样的恶都能被共情,正义的基石是否将崩塌?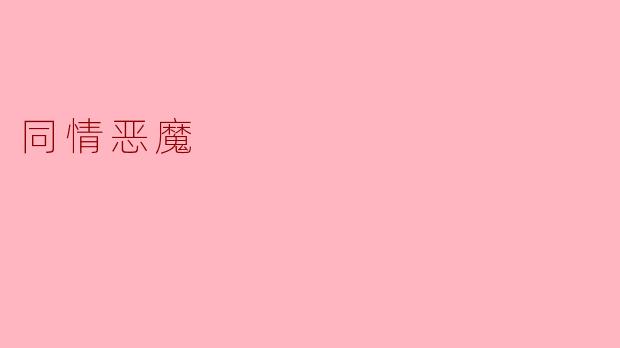
然而,拒绝一切同情亦是另一种极端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罪与罚》中借索尼娅之口质问:“谁有权审判?”真正的难题在于平衡:既要警惕对恶的美化,又要承认人性光谱的灰度。或许,“同情恶魔”的真正意义,不在于赦免其罪,而在于理解恶的起源——正如但丁在地狱中凝视撒旦的眼泪,不是为了拯救它,而是为了更清醒地守护人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