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荆棘花园里的蝴蝶》
她总在黄昏时推开那扇锈蚀的铁门,走进荒废的教堂后院。石缝里钻出的野蔷薇攀上圣母像的指尖,而他站在彩窗投下的紫红色光斑里,像一尊被信徒遗忘的圣徒雕塑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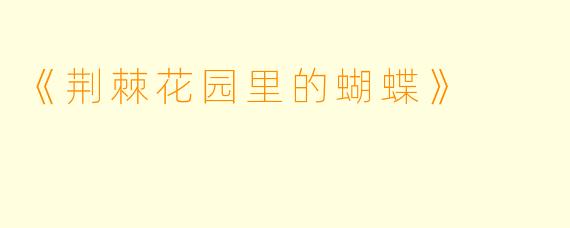
他们之间隔着三十年的岁月,和一本永远写不完的日记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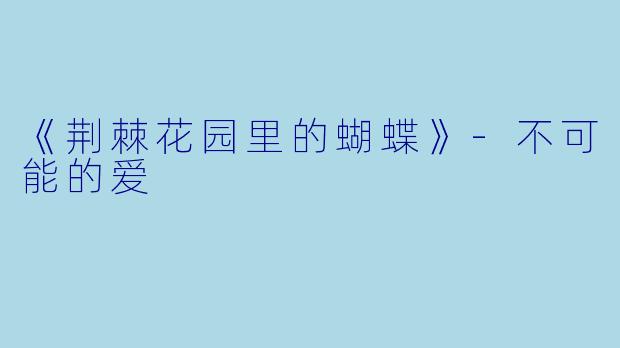
第一次相遇时,她的铅笔滚到他皮鞋边。他弯腰的瞬间,白发从耳后滑落,露出颈侧一道细长的疤——那是越战时期弹片留下的吻痕。而她刚从美院毕业,裙摆上沾着未干的丙烯颜料,像一团年轻的火。
"这里不该有蝴蝶。"他指着她素描本上的鳞翅目生物。彩窗上的圣徒眼睛里淌着铅灰色的雨,玻璃裂缝蜿蜒如地图上的国界线。
后来她才知道,他曾是战地摄影师,右眼装着义眼,左眼能看见亡灵。他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里,有她母亲的脸——1975年西贡陷落的清晨,一个穿奥黛的姑娘在直升机旋梯上松开婴儿的手。
雨季来临时,教堂地下室积了水。他们并排坐在管风琴旁,他教她用暗房药剂在底片上画十字。"显影液是时间,定影液是谎言。"他的声音沉在阴影里,手指划过她腕间淡青的血管,却在触碰的前一秒悬停成忏悔的姿势。
市政拆迁通知贴在告解室门上的那天,她撕下所有素描纸铺满告道。炭笔线条在雨中膨胀,那些未完成的肖像长出他的皱纹、他的伤疤、他永远挺直的脊背。而真正的他站在铁门外,风衣口袋里揣着去魁北克的车票。
野蔷薇疯长的六月,推土机碾碎了彩窗。工人们从地基里挖出个铁盒,里面只有枚变形的子弹壳,和一张烧焦的底片——依稀能辨出两个牵手的剪影,站在不存在于任何地图的国境线上。
